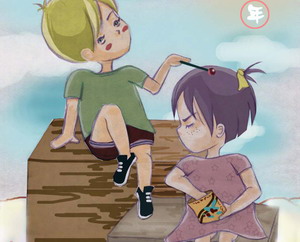
煎鹹魚
姥姥是在我35歲生日的前一天去世的,當時我正在外地求學。
我從出生後姥姥就一直照顧我。由於父母工作忙,我十一個月大時姥姥就把我帶回農村老家撫養,直到六歲半時回城上小學。由於從小沒在父母身邊,姥姥總覺得我很受委屈。70年代初農村生活很困難,主要是吃玉米麵、紅薯,白麵很少吃到,吃魚、肉就更少了,小孩專吃的營養品就更難買到。所以姥姥每逢趕集都要買些“好吃的”,還想法兒變著花樣做給我。當時的“好東西”不知吃了多少,都記不清了。但至今最使我難忘的是姥姥給我煎的鹹魚。
那時集上只有鹹魚賣。有一次姥姥買鹹魚回來,洗好後把它切成一寸見方的塊,粘裹上調好的麵糊,貼在大鍋裏用油慢慢煎,邊煎邊翻,還要時時往灶裏添柴禾,直到外面的麵糊變得又黃又脆後出鍋把它盛在盤子裏。此時我看著香,聞著香,吃起來就更香了。咬開外面鮮脆的麵糊,就可見到裏面的魚肉外表發紅,油油的;再咬一口,就露出白白的,軟軟的,嫩嫩的魚肉,還冒著騰騰的熱氣。我一頓可以吃兩三塊,還下許多飯。姥姥見我愛吃這樣做的魚,以後每逢趕集就准稱上一、二斤鹹魚帶回來。有時這個集上沒有,就趕到另一個集上去買,就這樣直到我回保定父母身邊上小學,但從此就很少能吃到這種煎鹹魚了。
在上小學時總覺得姥姥家才是我的家,而父母家只是我上學住的地方,所以一放假就回姥姥家去。姥姥還是照例要給我煎上幾次這樣的鹹魚吃。80年代末期我上大學期間放假再回姥姥家,姥姥不是給買鹹魚煎著吃了,而是給我買新鮮的活魚燉著吃。新鮮的活魚燉著吃當然很鮮美,但我還是喜歡姥姥煎的鹹魚。我跟姥姥說您給我煎鹹魚吃吧,但姥姥告訴我現在鹹魚已很難買到了,我小的那些年魚少,吃的人也少,如果不醃鹹放不住,所以才有鹹魚賣。現在每個集上都有新鮮的活魚賣,什麼時候吃什麼時候有,又有營養,誰還醃鹹魚,誰還買鹹魚!但至今三十多年過去了,已有妻小的我還是愛看那個焦黃色,愛聞那個鹹魚香,也愛吃那個鹹魚味。而這實際上是對幾十年來姥姥對我的養育和教誨之恩的懷念。而偶爾從超市買回久違的鹹魚,卻也永遠做不出記憶中的味道。
姥姥去世已五年多了。走在異鄉的校園小路上,在靜謐的夜晚仰望星空,我知道繁星中一定有一雙是姥姥慈祥的眼睛在望著我微笑。
姥姥您安息吧!
燒螞蚱
越快到晌午,我就越盼著三姨和小姨出工回來。我離不開姨們,雖然我那時經常不知道她們是什麼時候出門的,但姨們的回家,總是我快樂和驚喜的又一個開始。
記得當時姥姥家除了堂屋裏,在院子正對大門的地方也砌了一個灶,大概是夏天太熱吧,院子裏總要涼快些,況且這裏還是個風口。
終於盼到有姨們的說笑聲和腳步聲了,越來越近。我急忙跑到門邊迎著,期盼著帶著熟識親切泥土氣息的黑黑的姨們形象的出現。
門的光突然被擋住了,姨們魚貫而入。
“小忠玩呐。”
“嗯!”,我向姨們快活地點點頭,愉悅油然而生。三姨戴一頂黃色秫秸皮編制的尖頂草帽,顯得臉更黑了;而小姨只背著一頂黃舊的最普通的帶沿的草帽。
姨們卸掉扛著的鍁鋤和裝滿青草的筐。
“看這是什麼?”,小姨從青草裏抻出一團綠色的東西。
“螞蚱!”我欣喜地向小姨伸出雙臂。兩個被草纏住的大大的螞蚱還在努力掙紮。
“別急”,姨們笑著。“一會兒做飯時燒給你吃”。
“好啊,好啊!”我跟在姨們後面蹦蹦跳跳。“小姨,我還幫你拉風箱吧。”
……
大鐵鍋裏的水很快就燒開了,柴也基本燒盡了,堆了半灶膛帶著火星的柴灰。小姨用燒火棍扒拉扒拉柴灰,把一旁的大螞蚱投到灰槽裏,又用灰埋上。片刻之後,好像有一股香氣隱隱鑽進鼻孔。小姨略微俯下身專注地弄著燒火棍,我的兩隻眼睛也緊盯著被燒火棍撥得湧來湧去的泛著火星和輕煙的柴灰,香味越來越濃了……
小姨終於停止了撥動,左右分分漸暗漸涼的柴灰,兩個渾身棕黃色的螞蚱露了出來。螞蚱的須和翅膀都只剩下焦黃色的根,小腿散散地挺著,一碰就掉。
小姨用兩個細柴火棍把燒螞蚱夾出來,看了看,又聞了聞。“熟了嗎?”我怯怯地問。
小姨用手小心捏著掰了一下,淺紅的肉絲絲叉叉地露出來。
“我要,我要!”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拿。
“燙!”小姨笑著一下打開我的手,又愜意地聞了聞。
我只好乖乖在旁邊候著,看著小姨收拾灶台,給壺灌水,歸攏剩下的柴火。
“好了!”小姨遞給我一隻燒好的螞蚱。
我捧著這只燒螞蚱,先小心地扯下它的一條大腿放在嘴裏慢慢嚼,再一點點扯開品味,香甜化入心脾。“小姨,你也吃!”,“三姨,三姨!”我大聲喊著。
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一隻小小的燒螞蚱會讓我一生回味,更忘不掉的,是姨們對我的親情。
炸知了
秋生舅的輩分雖高,但他其實並不比我大多少,方臉龐,墩墩的身板。我始終不記得我為什麼總愛找他玩,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對我那麼特殊的好,好像一切順理成章、天生註定。
我高中前的夏天大抵都是在姥姥家度過的。在那時夏天聒噪的中午,我是經常要溜出家門的,四面八方那“知了”、“知了”的叫聲早已讓我心裏長草。我至今沒有形成午睡的習慣,不知是否與兒時的貪玩有關。
秋生舅早早等在外面,擎一根長秫秸,頂頭上栓一根馬尾,細如發絲。馬尾是纏了活套的,用來逮知了。我們冒著烈日,仰著頭,躡手躡腳地循樹前行,豎耳搜尋著周圍的動靜。
知了是很警覺的,覺察出一點兒動靜就會停止叫聲。但它也是健忘的,須臾的寧靜之後便又會肆無忌憚地歌唱,並漸漸高亢。我們這樣一點點靠近,彼此之間較量著耐心。終於,知了黑黑的、筆直爬附在樹幹上的身影暴露在眼前,薄薄的翅翼優雅地垂著,描繪著它主人特有的美麗。
我慢慢把馬尾套伸向它的頭部,我至今詫異它竟沒有多少反應,只不過偶爾停下來清清嗓子。馬尾套已經與它的頭平齊了,它還沒有動靜。我又把秫秸往上稍微舉了一舉,知了的頭部完全進入了“套程”。我屏住一口氣,“倏”地往下一拉,知了的頭部進入了馬尾套。受了驚嚇的知了“嗞啦”一聲尖叫,奮力啟動兩個翅膀,企圖離開這個危險的境地。但正是這個下意識逃離的行為,使它那兩個大眼睛突出的頭部緊緊套在了馬尾扣裏。
“逮住了!”我高興地喊。
秋生舅憨憨笑著向我敞開一個袋子。“走,我們到那面去”。
一中午的收穫可真不小,我們一共抓了五六隻呢。但也遺憾在我們的眼皮子底下飛跑了不少警惕性高的知了,但有些也是由於我們興奮過度,弄出了太大動靜。
……
晚上是又一種“圍獵”。
黑天裏,村街裏基本沒有什麼人。那時人們沒有晚上串門的習慣,晚飯後多半拿著大蒲扇在庭院裏閒聊納涼,看月亮,數星星。我們小孩子這時要了手電筒跑到街上,把燈光照到樹下地上,然後就用腿使勁踹樹。這時如果樹上有歇息的知了,多半會“劈裏啪啦”地掉到地上的光圈裏,我們捉它們起來毫不費力。這大概就是昆蟲的趨光性使然吧,但當時不懂,覺得很神奇。這種方式抓知了是很有效的,運氣好的話,一傍晚可以抓幾十隻。另外,晚上還經常可以捉到剛爬離地面的“知了猴”。
秋生舅讓我把知了都拿回去,扣在盆裏洗一洗,用淡鹽水泡一晚上。據大人講這是為了讓知了“吐吐髒”,也去去土腥子氣。
第二天早晨一睜眼,就感覺早有一股清香襲入鼻孔。姥姥和姨們在外面堂屋忙和著早飯,只等姥爺和舅舅出早工回來,而一盤尚泛著絲絲熱氣的炸知了早已放到桌上。那絲絲香氣縈繞盤旋,向我展示著至今難忘的天堂美味。
而吃起來的感覺和情景,現在卻怎麼也記不起來了。